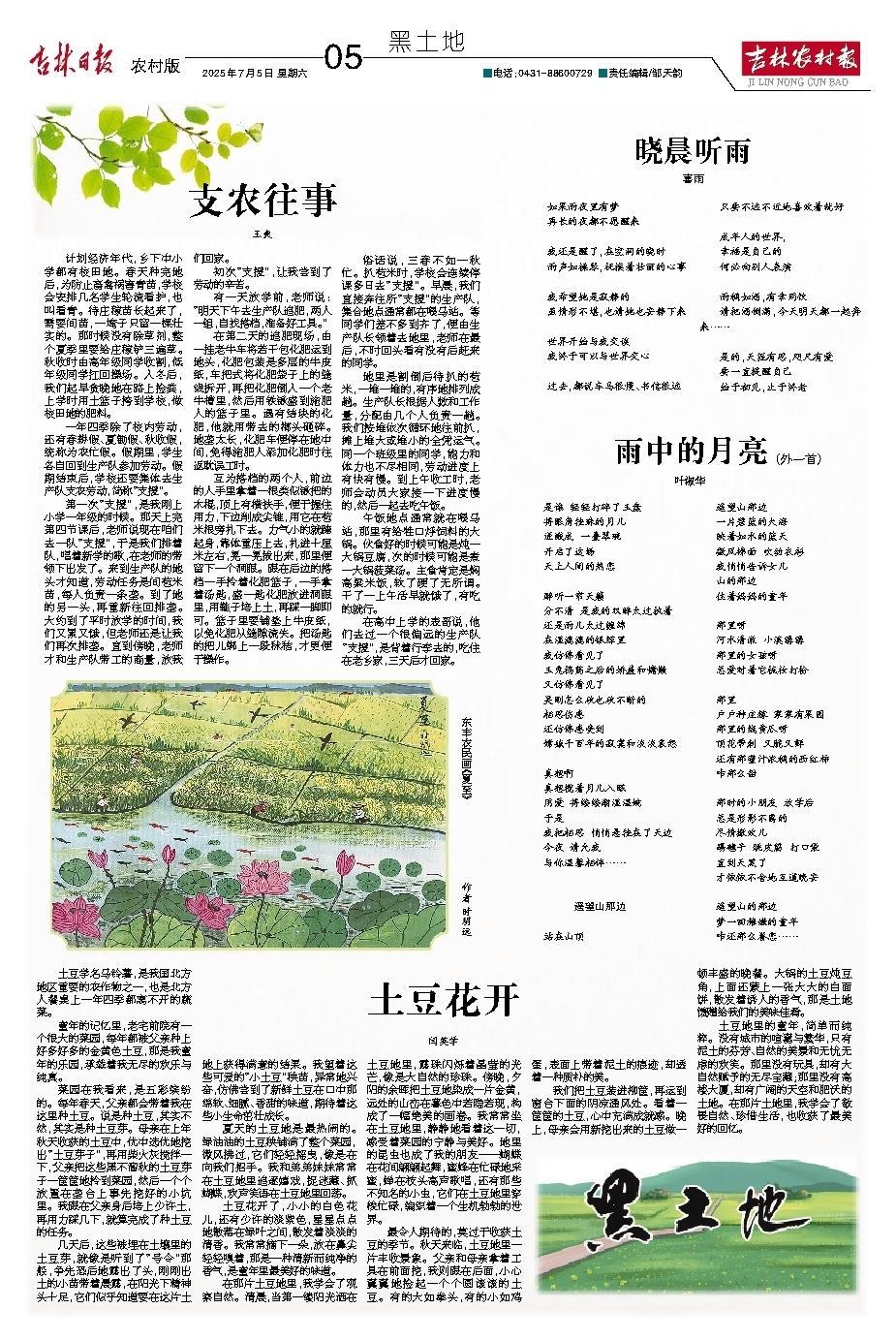计划经济年代,乡下中小学都有校田地。春天种完地后,为防止畜禽祸害青苗,学校会安排几名学生轮流看护,也叫看青。待庄稼苗长起来了,需要间苗,一埯子只留一棵壮实的。那时候没有除草剂,整个夏季里要给庄稼铲三遍草。秋收时由高年级同学收割,低年级同学扛回操场。入冬后,我们起早贪晚地在路上捡粪,上学时用土篮子挎到学校,做校田地的肥料。
一年四季除了校内劳动,还有春耕假、夏锄假、秋收假,统称为农忙假。假期里,学生各自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。假期结束后,学校还要集体去生产队支农劳动,简称“支援”。
第一次“支援”,是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。那天上完第四节课后,老师说现在咱们去一队“支援”,于是我们排着队,唱着新学的歌,在老师的带领下出发了。来到生产队的地头才知道,劳动任务是间苞米苗,每人负责一条垄。到了地的另一头,再重新往回排垄。大约到了平时放学的时间,我们又累又饿,但老师还是让我们再次排垄。直到傍晚,老师才和生产队带工的商量,放我们回家。
初次“支援”,让我尝到了劳动的辛苦。
有一天放学前,老师说:“明天下午去生产队追肥,两人一组,自找搭档,准备好工具。”
在第二天的追肥现场,由一挂老牛车将若干包化肥运到地头,化肥包装是多层的牛皮纸,车把式将化肥袋子上的缝线拆开,再把化肥倒入一个老牛槽里,然后用铁锹盛到施肥人的篮子里。遇有结块的化肥,他就用带去的榔头砸碎。地垄太长,化肥车便停在地中间,免得施肥人添加化肥时往返耽误工时。
互为搭档的两个人,前边的人手里拿着一根类似锹把的木棍,顶上有横扶手,便于握住用力,下边削成尖锥,用它在苞米根旁扎下去。力气小的就蹿起身,靠体重压上去,扎进十厘米左右,晃一晃拔出来,那里便留下一个洞眼。跟在后边的搭档一手拎着化肥篮子,一手拿着汤匙,盛一匙化肥放进洞眼里,用鞋子培上土,再踩一脚即可。篮子里要铺垫上牛皮纸,以免化肥从缝隙流失。把汤匙的把儿绑上一段秫秸,才更便于操作。
俗话说,三春不如一秋忙。扒苞米时,学校会连续停课多日去“支援”。早晨,我们直接奔往所“支援”的生产队,集合地点通常都在喂马站。等同学们差不多到齐了,便由生产队长领着去地里,老师在最后,不时回头看有没有后赶来的同学。
地里是割倒后待扒的苞米,一堆一堆的,有序地排列成趟。生产队长根据人数和工作量,分配由几个人负责一趟。我们按堆依次循环地往前扒,摊上堆大或堆小的全凭运气。同一个班级里的同学,能力和体力也不尽相同,劳动进度上有快有慢。到上午收工时,老师会动员大家接一下进度慢的,然后一起去吃午饭。
午饭地点通常就在喂马站,那里有给牲口烀饲料的大锅。伙食好的时候可能是炖一大锅豆腐,次的时候可能是煮一大锅菠菜汤。主食肯定是焖高粱米饭,软了硬了无所谓。干了一上午活早就饿了,有吃的就行。
在高中上学的表哥说,他们去过一个很偏远的生产队“支援”,是背着行李去的,吃住在老乡家,三天后才回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