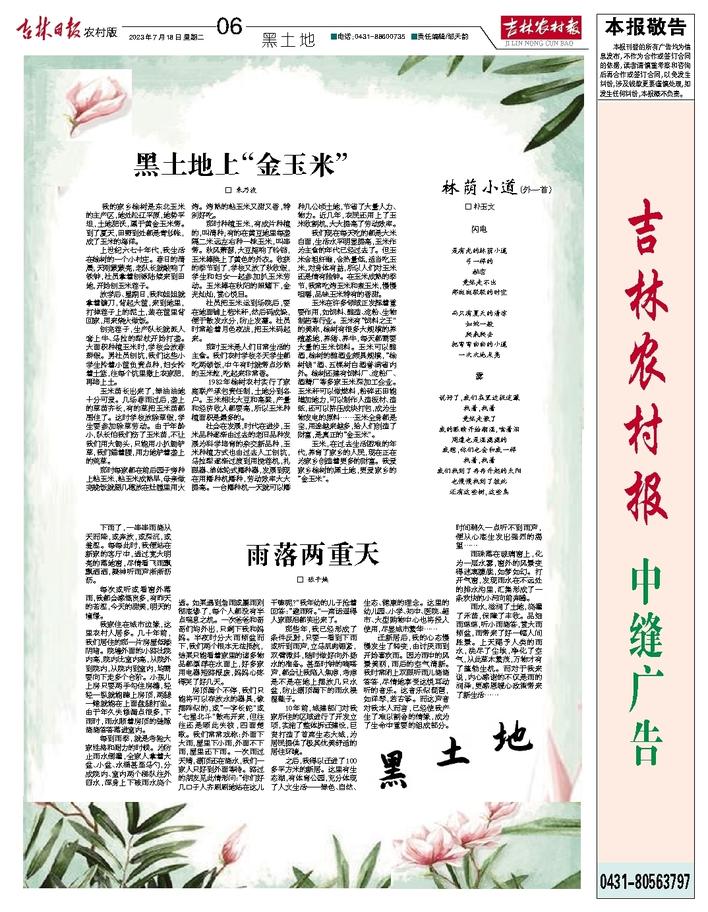□ 朱乃波
我的家乡榆树是东北玉米的主产区,地处松辽平原,地势平坦,土地肥沃,属于黄金玉米带。到了夏天,田野到处都是青纱帐,成了玉米的海洋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生活在榆树的一个小村庄。春日的清晨,天刚蒙蒙亮,老队长就敲响了铁钟,社员拿着刨锹陆续来到田地,开始刨玉米茬子。
放学后、星期日,我和姐姐就拿着镰刀,背起大筐,来到地里,打掉茬子上的泥土,装在筐里背回家,用来烧火做饭。
刨完茬子,生产队长就派人套上牛、马拉的犁杖开始打垄。大面积种植玉米时,学校会放春耕假。男社员刨坑,我们这些小学生拎着小筐负责点种,妇女拎着土篮,往每个坑里撒上农家肥,再培上土。
玉米苗长出来了,绿油油地十分可爱。几场春雨过后,垄上的草苗齐长,有的草把玉米苗都围住了。这时学校放除草假,学生要参加除草劳动。由于年龄小,队长怕我们伤了玉米苗,不让我们用大锄头,只能用小扒锄铲草,我们猫着腰,用力地铲着垄上的荒草。
那时每家都在前后园子旁种上粘玉米,粘玉米成熟早,母亲做完晚饭就掰几穗放在灶膛里用火烤。烤熟的粘玉米又甜又香,特别好吃。
那时种植玉米,有成片种植的,叫清种;有的在黄豆地里每垄隔二米远左右种一株玉米,叫串带。秋风萧瑟,大豆摇响了铃铛,玉米棒换上了黄色的外衣。收获的季节到了,学校又放了秋收假,学生和妇女一起参加扒玉米劳动。玉米棒在秋阳的照耀下,金光灿灿,赏心悦目。
社员把玉米运到场院后,要在地面铺上苞米秆,然后码成垛,便于散发水分,防止发霉。社员时常趁着月色夜战,把玉米码起来。
那时玉米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食。我们农村学校冬天学生都吃两顿饭,中午有时就带点炒熟的玉米粒,吃起来非常香。
1982年榆树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土地分到各户。玉米相比大豆和高粱,产量和经济收入都要高,所以玉米种植面积是最多的。
社会在发展,时代在进步,玉米品种逐渐由过去的老旧品种发展为科学培育的杂交新品种,玉米种植方式也由过去人工刨坑,马拉犁逐渐过渡到用搅茬机,扎眼器、单体轮式播种器,发展到现在用播种机播种,劳动效率大大提高。一台播种机一天就可以播种几公顷土地,节省了大量人力、物力。近几年,农民还用上了玉米收割机,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。
我们现在每天吃的都是大米白面,生活水平明显提高,玉米作为主食的年代已经过去了。但玉米含粗纤维,含热量低,适当吃玉米,对身体有益,所以人们对玉米还是情有独钟。在玉米成熟的季节,我常吃烤玉米和煮玉米,慢慢咀嚼,品味玉米特有的香甜。
玉米在许多领域正发挥着重要作用,如饲料、酿造、淀粉、生物制药等行业。玉米有“饲料之王”的美称,榆树有很多大规模的养殖基地,养猪、养牛,每天都需要大量的玉米饲料。玉米可以酿酒,榆树的酿酒业颇具规模,“榆树钱”酒、五棵树白酒誉满省内外。榆树还建有饲料厂、淀粉厂、酒精厂等多家玉米深加工企业。玉米秆可以做燃料,粉碎还田能增加地力,可以制作人造板材、造纸,还可以挤压成块打包,成为生物发电的原料……玉米全身都是宝,用途越来越多,给人们创造了财富,是真正的“金玉米”。
玉米,在过去生活困难的年代,养育了家乡的人民,现在正在为家乡创造着更多的财富。我爱家乡榆树的黑土地,更爱家乡的“金玉米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