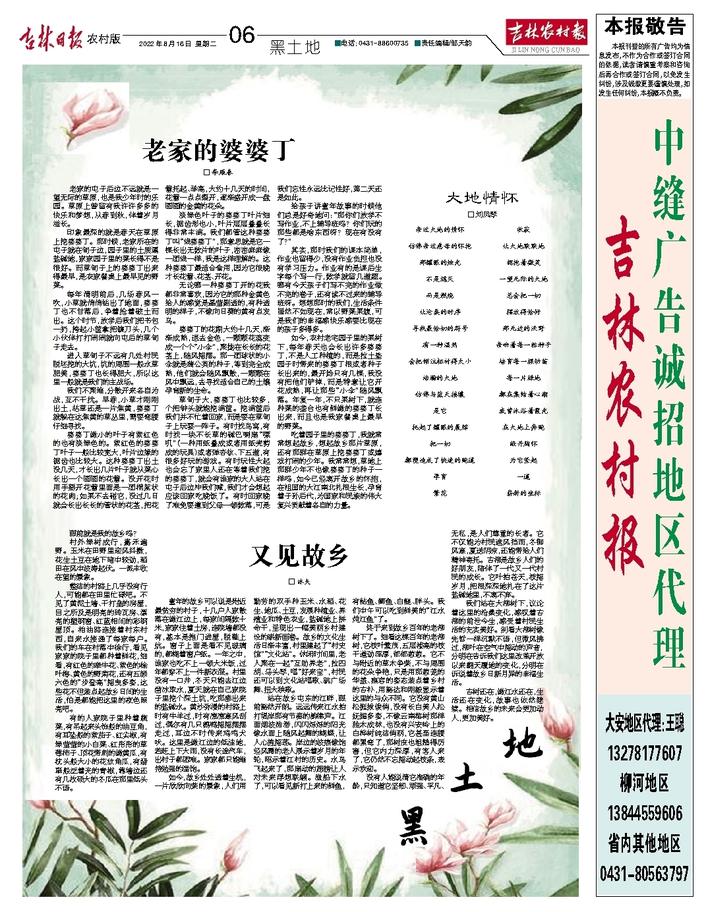□ 李雁春
老家的屯子后边不远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,也是我少年时的乐园。草原上曾留有我许许多多的快乐和梦想,从春到秋,伴着岁月滋长。
印象最深的就是春天在草原上挖婆婆丁。那时候,老家所在的屯子就在甸子边,园子里的土质属盐碱地,家家园子里的菜长得不是很好。而草甸子上的婆婆丁出来得最早,是农家餐桌上最早见的野菜。
每年清明前后,几场春风一吹,小草就悄悄钻出了地面,婆婆丁也不甘落后,争着抢着破土而出。这个时节,放学后我们把书包一扔,挎起小筐拿把镰刀头,几个小伙伴打打闹闹就向屯后的草甸子走去。
进入草甸子不远有几处村民脱坯挖的大坑,坑的周围一般水草肥美,婆婆丁也长得肥大,所以这里一般就是我们的主战场。
我们不聚堆,分散开来各自为战,互不干扰。早春,小草才刚刚出土,枯草还是一片焦黄,婆婆丁就躲在这焦黄的草丛里,需要弯腰仔细寻找。
婆婆丁嫩小的叶子有紫红色的也有淡绿色的。紫红色的婆婆丁叶子一般比较宽大,叶片边缘的锯齿也比较大。这种婆婆丁出土没几天,才长出几片叶子就从菜心长出一个圆圆的花蕾。没开花时用手掰开花蕾里面是一团棉絮状的花肉;如果不去碰它,没过几日就会长出长长的管状的花茎,把花蕾托起、举高,大约十几天的时间,花蕾一点点裂开,逐渐盛开成一盘圆圆的金黄的花朵。
淡绿色叶子的婆婆丁叶片细长,锯齿形也小,叶片层层叠叠长得非常丰满。我们都管这种婆婆丁叫“线婆婆丁”,那意思就是它一棵长出无数片的叶子,密密麻麻像一团线一样,我是这样理解的。这种婆婆丁最适合食用,因为它很晚才长花蕾、花茎、开花。
无论哪一种婆婆丁开的花我都非常喜欢,因为它的那种金黄色给人的感觉是晶莹剔透的,有种透明的样子,不像向日葵的黄有点发乌。
婆婆丁的花期大约十几天,渐渐成熟,退去金色,一颗颗花蕊变成一个个“小伞”,聚拢在长长的花茎上,随风摇摆。那一团球状的小伞就是蒲公英的种子,等到完全成熟,他们就会随风飘散,一颗颗在风中飘远,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土壤孕育新的生命。
草甸子大,婆婆丁也比较多,个把钟头就能挖满筐。挖满筐后我们并不忙着回家,而是要在草甸子上玩耍一阵子。有时找鸟窝,有时找一块不长草的碱巴喇扇“嘌叽”(一种用纸叠成或者用纸壳剪成的玩具)或者弹杏核、下五道,有很多好玩的游戏。有时玩性大起也会忘了家里人还在等着我们挖的婆婆丁,就会有谁家的大人站在屯子后边冲我们喊,我们才会想起应该回家吃晚饭了。有时回家晚了难免要遭到父母一顿数落,可是我们忘性永远比记性好,第二天还是如此。
给孩子讲童年故事的时候他们总是好奇地问:“那你们放学不写作业,不上辅导班吗?你们玩的那些都是啥东西呀?现在有没有了?”
其实,那时我们的课本简单,作业也留得少,没有作业负担也没有学习压力。作业有的是课后生字每个写一行,数学就留几道题。哪有今天孩子们写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卷子,还有读不过来的辅导班呀。想想那时的我们,生活条件虽然不如现在,常以野菜果腹,可是我们的幸福感快乐感要比现在的孩子多得多。
如今,农村老宅园子里的果树下,每年春天也会长出许多婆婆丁,不是人工种植的,而是拉土垫园子时带来的婆婆丁根或者种子长出来的,最开始只有几棵,我没有把他们铲掉,而是特意让它开花成熟,再让那些“小伞”随风飘落。年复一年,不只果树下,就连种菜的垄台也有鲜嫩的婆婆丁长出来,而且也是我家餐桌上最早的野菜。
吃着园子里的婆婆丁,我就常常想起故乡,想起故乡那片草原,还有那群在草原上挖婆婆丁或嬉戏打闹的少年。我常常想,草地上那群少年不也像婆婆丁的种子一样吗,如今已经离开故乡的怀抱,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扎根生长,孕育着子孙后代,为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各自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