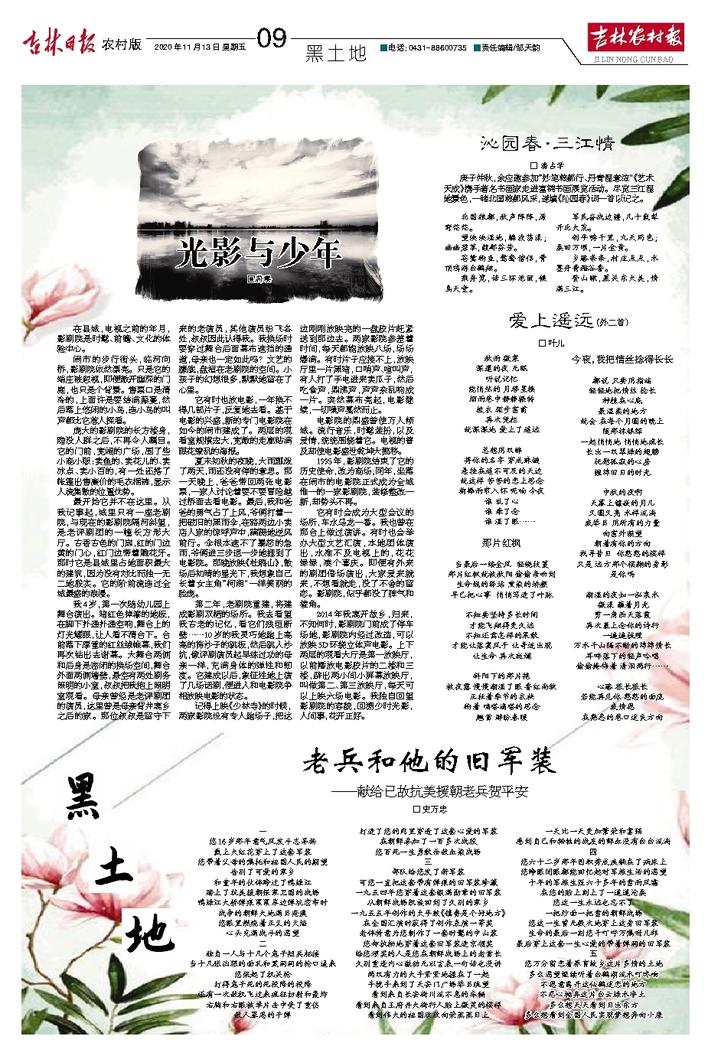□莉璎
在县城,电视之前的年月,影剧院是时髦、前瞻、文化的体验中心。
闹市的步行街头,临河向桥,影剧院依然漂亮。只是它的端庄被忽视,即便敞开幽深的门庭,也只是个背景。售票口是清冷的,上面许是要结满藤蔓,然后落上悠闲的小鸟,连小鸟的叫声都比它惹人探看。
庞大的影剧院的长方楼身,隐没人群之后,不再令人瞩目。它的门前,宽阔的广场,围了些小商小贩:卖鱼的、卖花儿的、卖冰点、卖小百的,有一处还搭了帐篷出售廉价的毛衣棉裤,显示人流集散的位置优势。
最开始它并不在这里。从我记事起,城里只有一座老剧院,与现在的影剧院隔河斜望,是老评剧团的一幢长方形大厅。古香古色的门扉,红的门边黄的门心,红门边带着雕花牙。那时它是县城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,因为没有对比而独一无二地殷实。它的阶前流连过全城最盛的浪漫。
我4岁,第一次随幼儿园上舞台演出。暗红色掉漆的地板,在脚下扑通扑通空响,舞台上的灯光耀眼,让人看不清台下。台前落下厚重的红丝绒帷幕,我们再次钻出去谢幕。大舞台两侧和后身是密闭的换场空间,舞台外面两侧墙壁,悬空有两处剧务照明的小室,叔叔把我抱上照明室观看。母亲曾经是老评剧团的演员,这里曾是母亲背井离乡之后的家。那位叔叔是留守下来的老演员,其他演员纷飞各处,叔叔因此认得我。我换场时要穿过舞台后面幕布遮挡的通道,母亲也一定如此吗?文艺的朦胧,盘桓在老剧院的空间。小孩子的幻想很多,默默地留在了心里。
它有时也放电影,一年换不得几部片子,反复地去看。基于电影的兴盛,新的专门电影院在如今的闹市建成了。两层的观看室规模宏大,宽敞的走廊贴满眼花缭乱的海报。
夏末初秋的夜晚,大雨瓢泼了两天,雨还没有停的意思。那一天晚上,爸爸带回两张电影票,一家人讨论着要不要冒险越过桥面去看电影。最后,我和爸爸的勇气占了上风,爷俩打着一把破旧的黑雨伞,在路两边小卖店人家的惊呼声中,蹒跚地逆风前行。伞根本遮不了暴怒的急雨,爷俩进三步退一步地捱到了电影院。那晚放映《杜鹃山》,散场后初晴的星光下,我想象自己长着女主角“柯湘”一样美丽的脸庞。
第二年,老剧院重建,将建成影剧双栖的场所。我去看望我古老的记忆,看它们残垣断壁……10岁的我灵巧地跑上高高的筛沙子的跳板,然后跳入沙坑,像评剧演员起早练过功的母亲一样,充满身体的弹性和韧度。它建成以后,象征性地上演了几场话剧,便进入和电影院争相放映电影的状态。
记得上映《少林寺》的时候,两家影院设有专人跑场子,把这边刚刚放映完的一盘胶片赶紧送到那边去。两家影院参差着时间,每天都能放映八场,场场爆满。有时片子应接不上,放映厅里一片黑暗,口哨声、喧叫声,有人打了手电进来卖瓜子,然后吃食声,鼎沸声,声声杂乱响成一片。突然幕布亮起,电影继续,一切噪声戛然而止。
电影院的鼎盛曾使万人倾城。流行音乐,时髦装扮,以及爱情,统统围绕着它。电视的普及却使电影盛世乾坤大挪移。
1995年,影剧院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,改为商场;同年,坐落在闹市的电影院正式成为全城惟一的一家影剧院,装修整改一新,却势头不再。
它有时会成为大型会议的场所,车水马龙一番。我也曾在那台上做过演讲。有时也会举办大型文艺汇演,本地团体演出,水准不及电视上的,花花绿绿,凑个喜庆。即便有外来的剧团借场演出,大家爱来就来,不想看就走,没了不舍的留恋。影剧院,似乎都没了脾气和棱角。
2014年我离开故乡,归来,不知何时,影剧院门前成了停车场地,影剧院内经过改造,可以放映3D环绕立体声电影。上下两层的观看大厅是第一放映厅,以前播放电影胶片的二楼和三楼,辟出两小间小屏幕放映厅,叫做第二、第三放映厅,每天可以上映六场电影。我独自回望影剧院的容貌,回溯少时光影,人间事,花开正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