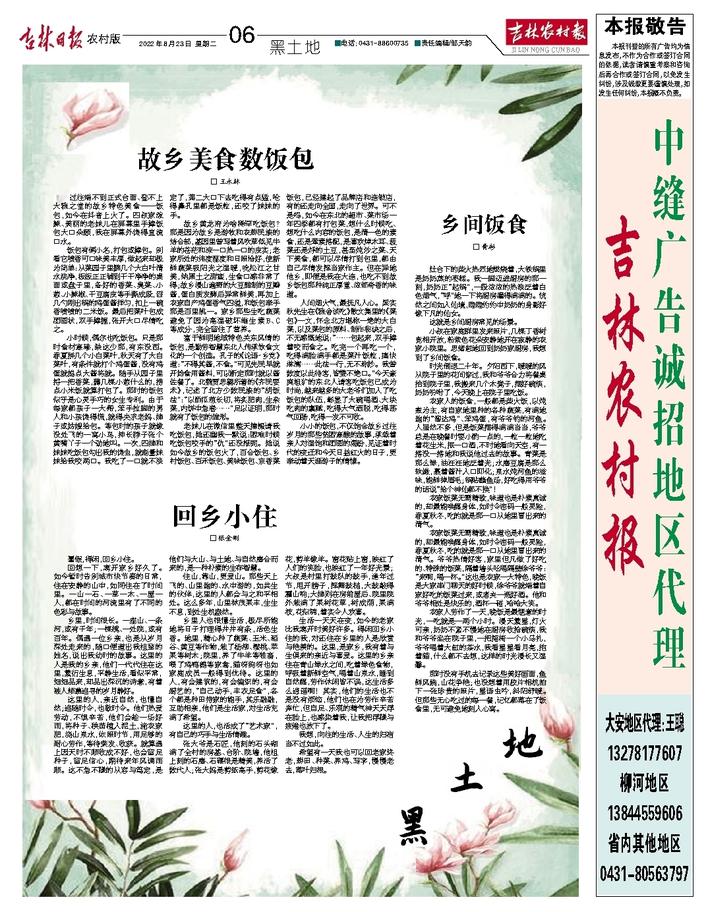□ 王永林
过往端不到正式台面、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故乡特色美食——饭包,如今在抖音上火了。四叔家泼辣、美丽的老妹儿在屏幕里手捧饭包大口朵颐,我在屏幕外馋得直流口水。
饭包有俩小名,打包或捧包。别看它喷香可口味美丰厚,做起来却极为简单:从菜园子里擗几个大白叶清水洗净,板板正正铺到干干净净的桌面或盘子里,备好的香菜、臭菜、小葱、小辣椒、干豆腐皮等手撕成段,舀几勺刚出锅的鸡蛋酱拌匀,扣上一碗香喷喷的二米饭。最后把菜叶包成团圆状,双手捧握,张开大口尽情吃之。
小时候,偶尔也吃饭包。只是那时食材寒碜,缺这少那,有东没西。春夏拼几个小白菜叶,秋天有了大白菜叶,有条件就打个鸡蛋酱,没有鸡蛋就捣点大酱将就。随手从园子里捋一把香菜,薅几棵小葱什么的,捞点小米饭就算打包了。那时的饭包似乎是心灵手巧的女生专利。由于每家都孩子一大帮,笨手拉脚的男人和小孩馋得慌,就得央求老妈、婶子或姑嫂给包。等包时的孩子就像没处飞的一窝小鸟,抻长脖子张个黄嘴丫子一个劲地叫。一次,四婶和妹妹吃饭包勾出我的馋虫,就商量妹妹给我咬两口。我吃了一口就不淡定了,第二大口下去吃得有点猛,呛得鼻孔里都是饭粒,还咬了妹妹的手。
故乡黄龙府为啥稀罕吃饭包?那是因为故乡是游牧和农耕民族的结合部,基因里曾写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和凉一口热一口的皮实;老家所处的纬度湿度和日照恰好,使新鲜蔬菜吸阳光之温暖,吮松江之甘美,纳黑土之甜蜜,生食口感非常了得;故乡漫山遍野的大豆酿制的豆瓣酱,蛋白质发酵后异常鲜美,再加上农家自产鸡蛋香气四溢,和饭包牵手那是百里挑一。家乡那些生吃蔬菜避免了因为高温破坏维生素B、C等成分,完全留住了营养。
富于鲜明地域特色关东风情的饭包,是勤劳智慧东北人传承饮食文化的一个创造。孔子的《论语·乡党》道:“不得其酱,不食。”可见先民早就开始食用酱料,可以断定那时就以酱佐餐了。北魏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,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“胡饭法”:“以酢瓜菹长切,将炙肥肉,生杂菜,内饼中急卷……”足以证明,那时就有了饭包的雏形。
老妹儿在微信里整天撺掇请我吃饭包,她还幽我一默说:困难时候吃饭包咬手的“仇”还没报呢。她说如今故乡的饭包火了,百合饭包、乡村饭包、百禾饭包、美味饭包、京香菜饭包,已经建起了品牌店和连锁店,有的还走向全国,走向了世界。可不是吗,如今在东北的超市、菜市场一年四季都有打包菜,想什么时候吃、想吃什么内容的饭包,是清一色的素食,还是荤素搭配,是喜欢焯木耳、菠菜还是烀的土豆,甚至炖炒之菜、天下美食,都可以尽情打到包里,都由自己尽情发挥当家作主。但在异地他乡,即便是我在大连,也吃不到故乡饭包那种纯正厚重、浓郁奇香的味道。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梁实秋先生在《雅舍谈吃》散文集里的《菜包》一文,怀念北方堪称一绝的大白菜,以及菜包的原料、制作秘诀之后,不无感慨地说:“……包起来,双手捧着咬而食之。吃完一个再吃一个,吃得满脸满手都是菜汁饭粒,痛快淋漓……此法一行,无不称妙。我曾数度以此待客,皆赞不绝口。”今天豪爽粗犷的东北人请客吃饭包已成为时尚,越来越多的大老爷们加入了吃饭包的队伍,彰显了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的禀赋,吃得大气洒脱,吃得荡气回肠,吃得一发不可收。
小小的饭包,不仅饱含故乡过往岁月的那些贫困寒酸的故事,承载着亲人对温饱和团圆的渴盼,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今天日益红火的日子,更牵动着天涯游子的情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