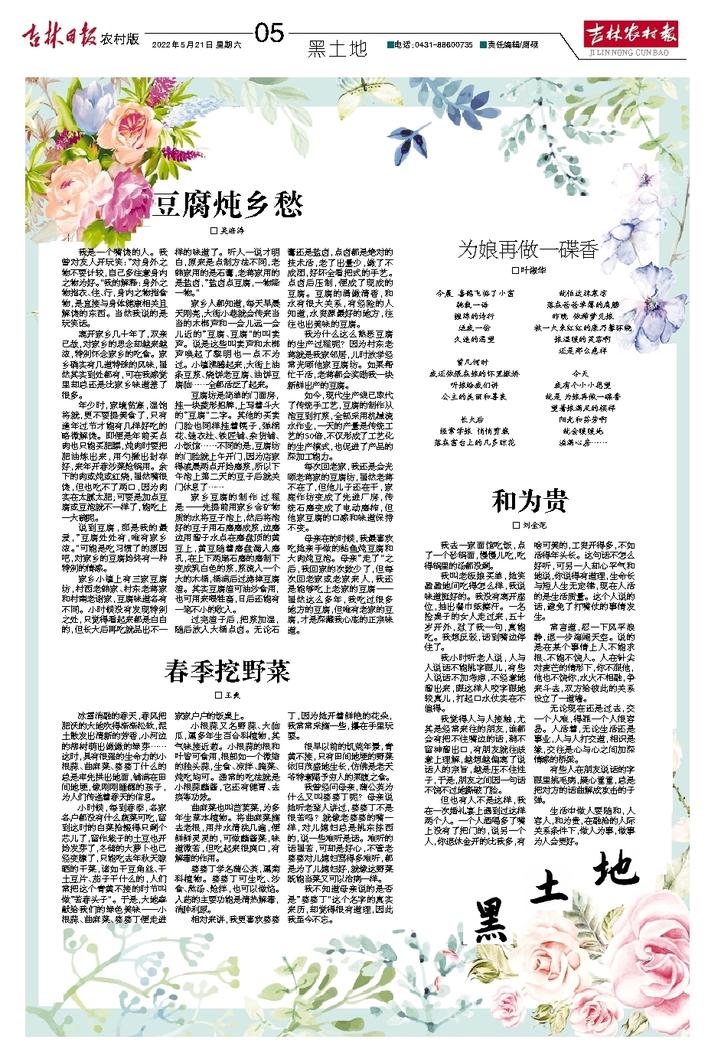□ 吴海涛
我是一个嘴馋的人。我曾对友人开玩笑:“对身外之物不要计较,自己多注意身内之物为好。”我的解释:身外之物指衣、住、行,身内之物指食物,是直接与身体健康相关且解馋的东西。当然我说的是玩笑话。
离开家乡几十年了,双亲已故,对家乡的思念却越来越浓,特别怀念家乡的吃食。家乡确实有几道特殊的风味,虽然其实到处都有,可在我感觉里却总还是比家乡味道差了很多。
年少时,家境贫寒,温饱将就,更不要提美食了,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有几样好吃的略微解馋。即便是年前买点肉也只能买肥膘,炖肉时要把肥油炼出来,用勺撇出封存好,来年开春炒菜炝锅用。余下的肉或炖或红烧,虽然嘴很馋,但也吃不了两口,因为肉实在太腻太肥;可要是加点豆腐或豆泡就不一样了,能吃上一大碗呢。
说到豆腐,那是我的最爱,“豆腐处处有,唯有家乡浓。”可能是吃习惯了的原因吧,对家乡的豆腐始终有一种特别的情感。
家乡小镇上有三家豆腐坊,村西老韩家、村东老蒋家和村南老谢家,豆腐味道各有不同。小时候没有发现特别之处,只觉得看起来都是白白的,但长大后再吃就品出不一样的味道了。听人一说才明白,原来是点制方法不同,老韩家用的是石膏,老蒋家用的是盐卤,“盐卤点豆腐,一物降一物。”
家乡人都知道,每天早晨天刚亮,大街小巷就会传来当当的木梆声和一会儿远一会儿近的“豆腐、豆腐”的叫卖声。说是这些叫卖声和木梆声唤起了黎明也一点不为过。小镇沸腾起来,大街上油条豆浆、烧饼老豆腐、油饼豆腐脑……全都活泛了起来。
豆腐坊是简单的门面房,挂一块菱形招牌,上写着斗大的“豆腐”二字。其他的买卖门脸也同样挂着幌子,弹棉花、缝衣社、铁匠铺、杂货铺、小饭馆……不同的是,豆腐坊的门脸就上午开门,因为店家得凌晨两点开始磨浆,所以下午泡上第二天的豆子后就关门休息了……
家乡豆腐的制作过程是——先提前用家乡含矿物质的水将豆子泡上,然后将泡好的豆子用石磨磨成浆,边磨边用溜子水点在磨盘顶的黄豆上,黄豆随着磨盘漏入磨孔,在上下两扇石磨的磨制下变成乳白色的浆,浆流入一个大的木桶,桶满后过滤掉豆腐渣。其实豆腐渣可油炒食用,也可用来喂牲畜,日后还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过完渣子后,把浆加温,随后放入大桶点卤。无论石膏还是盐卤,点卤都是绝对的技术活,老了出量少,嫩了不成团,好坏全看把式的手艺。点卤后压制,便成了现成的豆腐。豆腐的滑嫩清香,和水有很大关系,有经验的人知道,水资源最好的地方,往往也出美味的豆腐。
我为什么这么熟悉豆腐的生产过程呢?因为村东老蒋就是我家邻居,儿时放学经常光顾他家豆腐坊。如果帮忙干活,老蒋都会奖励我一块新鲜出产的豆腐。
如今,现代生产线已取代了传统手工艺,豆腐的制作从泡豆到打浆,全部采用机械流水作业,一天的产量是传统工艺的50倍,不仅形成了工艺化的生产模式,也促进了产品的深加工能力。
每次回老家,我还是会光顾老蒋家的豆腐坊,虽然老蒋不在了,但他儿子还在干,家庭作坊变成了先进厂房,传统石磨变成了电动磨榨,但他家豆腐的口感和味道保持不变。
母亲在的时候,我最喜欢吃她亲手做的鲇鱼炖豆腐和大肉炖豆泡。母亲“走了”之后,我回家的次数少了,但每次回老家或老家来人,我还是能够吃上老家的豆腐——虽然这么多年,我吃过很多地方的豆腐,但唯有老家的豆腐,才是深藏我心底的正宗味道。